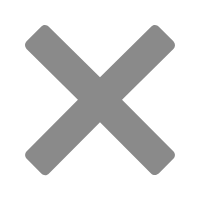-
潜龙传奇
第13章寻宝记(12)
“嗯!笑天……为师之前已经到过了天罗境,按照玄武神尊的意思,九龙法阵现在崩塌一角,恐怕戾气外泄人间世道不稳,我们龙门隐宗当遣派门人弟子入世平息此难。而为师和你师兄看守这地宫不便擅离,且我二人已然丹鼎成就脱了凡体,再轻易入世恐世人无知多生变故,所以……这重任还希望你能担起来才好。”
马真一这话说得半真半假,其实他原本是想把笑天收归门下继承地宫值守之责,以便日夜教导这个和龙门颇有缘法的弟子。奈何玄武点破玄机,透漏出笑天命格特异,前半生注定六亲单薄孤苦无依、流离颠沛诸多劫难,若是强行留在地宫,恐怕九龙邪祟借他心志不坚而寻机生事,当先入世磨砺心志苦练修行才是正途。另则玄武真灵认定他和自己有缘,已将地书残卷十三篇藏于他神识之中,拟借他之手将此秘典流传于世,有心造就他一番功果,所以马真一也不愿因一己私念而断送了他大好前程了。
“那……就听师父的,不过俺可不像你们有本事,出去以后恐怕误了大事的。”笑天愣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自己其实没和这神仙师父学过什么能耐,实在没什么底气可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
“呵呵……你个小子是变着法儿问我要好处哩?行吧,我看你和我那手边两件法器算是投契,就先传你一些基本的法门……,至于更高深的知识,你已经从神尊那里得了莫大好处,日后你自有机缘知晓……嗯,附耳过来。”马真一笑着点了点头,叫笑天把头凑过来,低声细语嘱咐了半晌。说完之后也不问他记没记住,只叭地一声,重重往他头顶一拍,大喝了一声:“法不传六耳,孺子可教否?”
笑天正听得一团乱麻不知头绪时,忽然被一掌打得眼冒金星,情不自禁说了一句:“受教!”
之后便见马老道把两件宝贝往他手里一塞,接着含笑起身飘然而去,旁边只剩下郭常霖满脸都是羡慕的神情……
发了一阵愣,突然感觉脑袋里多了不少不明所以的法诀和理论,脸上由不得变颜变色,好半天才长长出了一口大气。
“师……师兄,敢情这跟着老师学艺就这么简单,往头上拍一把掌就会了……”
郭常霖愕然片刻,突然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一边捂着肚子忙不迭地往门外走,一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于……别……人复杂,于你……就……就是这么简单!哈哈哈哈哈……日后你慢慢也就明白了……哈哈……我的个师弟呦……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走出了没几步,他突然又返了回来,走到近前往笑天手里塞了几个小瓶和一小包东西,笑眯眯说道:“我这个师兄穷得要死,随身也只这些救急的伤药,还有些小玩意儿连同我的修行心得一并送给你,别嫌弃,先给你安排那畜生送你出去,你先歇一会儿,就过来法台吧!”
说完了,郭常霖冲着笑天眨眨眼,然后就匆匆出门去了。
“这一个两个……究竟在打什么哑谜?”掂了掂手里的小包袱,随手打开注目观看,不由得让笑天顿时大吃了一惊!
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只巴掌大的黄翡翠蟠龙钮印章胚,入目通体润泽细腻,翡色浓艳,美艳照人,整体用料完整,毫无瑕疵,一束白翠映于其中,仿如翡色与白翠深浅相结合,风韵雅致,不由令人感叹自然造物之神奇。
旁边却是一只翡翠竹节,那绿色浓艳纯正均匀,质地细腻,油润光滑,雕工简单大方,别具匠心绝对堪称上品。
这两件玉器皆用一块红色绒布盛在一只尺余见方的乌木盒当中,轻轻端起木盒,只觉手中温润细腻、边角光洁,在灯下隐约看过去,触目惊心竟是一片金色流光溢彩,恍如夕阳晚照水波荡漾,兼有阵阵清香扑鼻,非但丝毫不逊色于盒中宝物,更于两件玉器相映成趣,颇为不俗。
但最让笑天心动地却是在盒底端端正正压着一本毛边纸的册子,打开看看,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字迹,其间点画沉厚,结字茂密,姿态奇宕,竖挺方折,饶具金石之气趣。
这里内容写得都是郭常霖修行之中的一些心得和当初行走天下的笔记,措辞恭谨扼要,对于此刻的笑天而言,却是比盒中那两件玉器更加实用和弥足珍贵了。
“这位郭师兄看似疯疯癫癫的,对我倒是真好……可惜就是在这地下困得太久,总是神神叨叨的。”
笑天心满意足的把那包袱斜背在身后,却单独把笔记和法器掖进了怀里,贴身放好。轻轻拍了拍胸口,他又跳了两下,感觉没什么牵挂松散的地方……随即连忙往法台那里赶了过去。
一路到了九龙法台阵口,只见蛰龙憨宝蜷曲着身体,正把大大的脑袋垂下来听郭常霖讲话,诧异地却是没看见马真一的人影。
“师兄?”
“来了,好……我们这就走吧。”看见笑天过来,郭常霖点了点头,一拍憨宝的脖子轻飘飘坐到了它的后颈处,单手抓着龙角,一只手则向着笑天伸了过来。
“师父他……他没过来?”笑天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有些犹豫了,似乎在这个空荡荡的地宫里,他突然找到了一直都在向往的那份温暖,几乎他有一种冲动想要反悔自己的决定了。
“日后相见有期,却是不必非拘泥于儿女情长,师父有话,叫你若是到了想要回来的时候,捏碎这里面的玉符即可。”说着话,郭常霖把一个玉扳指丢了过来。
“里面?”笑天一愣,把那扳指往大拇指上一扣,突然只觉指根一紧,那玉扳指竟是自动缩紧和拇指牢牢合在了一起,虽然也勉强可以转动,但是要想取下来,却是不可能了。
“闭目,凝神,将手中那扳指轻轻转动……”
耳边传来郭常霖的言语,笑天连忙依言照做,才闭上眼睛手里刚转动扳指时,顿时眼前出现了一个约有半间屋子大小的光亮空间,靠角落地上放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一只铜炉,正中放置了条案,上面摆着三支玉圭,五面小旗,一只拂尘,一把木剑还有一摞黄色的符纸。
“那桌子上是符箓,法旗和乾坤玉符,衣箱里有法衣和法冠,都是师父准备的,以备你日后不时之需……”
笑天看向玉圭,心念一动,立刻感觉手中一沉,再睁开眼时那物件已经到了手里,不禁又惊又喜,再试着闭目凝神,那玉圭又再次放回到了原处!
“这扳指……哈哈哈……真是个宝贝!”
笑天乐得前仰后合,不住把那里面的东西来回倒腾,到最后索性把随身的器物全部都挪到了那扳指里面,身子也随之一轻。
“这是我隐宗的随身之宝,唤做须弥芥子,其中诸多妙用却是待你自己领悟,以后你慢慢也就明白了。”
“嗯。”
笑天心里一紧,突然明白自己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有些留恋地看了看周围,默默无语,一把抓住了郭常霖的手臂,双腿一使劲,便被对方提到了蛰龙背上。
“走……”
随着郭常霖大手一拍龙头,憨宝嗷地吼了一声,整个身体翻卷而起,四只爪子划动飘摆,摇摇荡荡直上半空,望着天穹那层水幕冲了过去……
……
……
还是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刚交农历八月,脱下单衣单裤仍然感觉到燥热袭人,被侄子伺候着吃过了午饭,老神头躺在床上。
经过了那件事之后,他的精神差了不少,所以每天午饭后他都要歇息那么一会儿,有时短到只眨一眨眼眯盹儿一下,不过今天老神头刚躺下就滋滋润润地迷糊了。
他梦见自己在山顶上,头顶呼地一个闪亮,满天流火纷纷下坠,有一团正好落到他的胸膛上烧得皮肉吱吱吱响,接着就从坡上翻跌到了乱石砬子里。惊醒后他已经跌落在炕下的砖地上,摸摸胸脯,这里完好无损并没有什么流火灼烧的痕迹,而心窝里头着实火烧火燎,像有火焰呼呼喷出,灼伤了喉咙口腔和舌头,全都变硬了变僵了变得干涸了。
外面的侄子们大约听到响声跑进屋来,却无论抱他拉他都无法使他爬到炕上去,费了不少力气,三个人总算是把他抬到炕上,一齐俯下身焦急而情切地询问哪儿出了毛病。
可这时候的老神头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粗硬的指甲抓扒自己的脖颈和胸脯,嘴里发出嗷嗷嗷呜呜呜,仿佛狗受委屈时一样的叫声。
几个人全都急傻了,只有刚刚进门的林家大爷林茂财急急火火地喊着:“快!把孙八指叫来……”
孙八指在山下镇子西门外,胡同里有间小门脸,他坐堂就诊,兼营着自己熬制的中药。
听来人说了病状,孙八指心里就明白了八九成,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皮包挂到腰带上,急忙赶到了病人家来。
孙八指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土郎中,他穿着一身灰布长衣,肥肥大大的黑裤子,一抬足一摆手那裤子就就忽悠悠地抖。
三十多岁年纪,头发油亮的如同打过蜡,脸上也是红光满面。孙八指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有钱人用轿车拉他他去,穷人拉一头毛驴接他他也去,连毛驴也没有的人家请他他就步着去了。
人给他封金赏银他照收不拒,穷人家给几个玉米棒子他也坦然装入衣兜,穷得一时拿不出钱的人他不逼不索甚至连问也不问,任就诊者自己到手头活便的时候给他送来,所以他在这山沟沟里一向落下了好名望。凡经过他救活性命的幸存者和许多纯粹仰慕医德的乡里人送来的匾额挂满了半堵墙面。
孙八指坐上那张蹭得锃亮的木制凳子,他不多说话倒不怠慢焦急如焚的患者。他永远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看好病是这副模样,看不好也是这副模样,看死了人还是这副模样,他给任何病患和家属的印象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因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孙八指医术平庸,他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也是莫可奈何。
孙八指此时不动声色,冷着脸摸了左手的脉又捏了捏肚腹,然后用双手掀开的嘴巴,轻轻“嗯”了一声就转过头问林茂财:“有烧酒没有?”
旁边四小子连声应着“有有有”,转身就把一整瓶烧酒取来了。
孙八指又要来一只青瓷碗,把烧酒咕嘟嘟倒入碗里,用眼睛示意将酒点燃。
四小子满面虚汗,颤抖的双手捏着火柴却打不出火花来。
孙八指接过手只一下就打燃了火柴,噗地一下子点燃了烧酒。接着他又从裤腰带上解下皮夹再揭开暗扣,露出一排刀子锥子挑钩粗针和一只闪闪发光的三角刮刀。
孙八指取出一根麦秆粗的钢针和一块钢板,一齐放到烧酒燃起的蓝色火焰上烧烤,然后吩咐几个小伙子压死老汉的双手,尤其是要压紧双腿,特别叮嘱挟紧老神头的头和脖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松动。
一切都严格按照孙八指的嘱咐进行着……
孙八指把那块钢板塞进老神头的口腔,用左手食指一分就变成一个V形的撑板,把老神头的嘴撬撑到极限,右手里那根正在烧酒火焰上烧得发红变黄的钢针一下戳进喉咙,旁人尚未搞清怎么一回事,钢针已经拔出,只见老神头嘴里冒出一股青烟,散发着皮肉焦灼的奇臭气味。
孙八指一边擦拭刀具一边说:“放开手吧,完事了。”随之吹熄了烧酒碗里的火苗儿。
老神头像麻花一样扭曲的腿脚手臂松弛下来,散散伙伙地随意摆置在炕上一动不动,口里开始淌出一股乌黑的粘液,看了令人恶心,林茂财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
这时候,老神头渐渐睁开眼睛。
四个人同时发现了这一伟大的转机,眼睛里有一缕表示生命回归的活光,像是阴霾的云缝泄下一缕柔和又是生机勃勃的阳光。
三个人同时惊喜地“呀”一声,不约而同地转过溢着泪花的眼来看着孙八指。
孙八指还是惯常那副模样,说:“给灌一点凉开水。”
三个人手忙脚乱又是小心翼翼地给那个阔大的嘴巴灌了几勺开水,老神头竟然神奇地坐了起来,抓住孙八指的手长长叹了口气:“唉……”
几个人惊呼了声,一起围了过来。
老神头虚弱地说:“去,给孙先生倒水去。”
四小子慌忙离去了,灶间传来很响的添水声和风箱声。孙八指坐下也不说话,接过主家递给他的香烟就悠悠吸起来。
才不过半支烟,老神头的手脚随着身子的突然仰倒又扭起了麻花,而且更加剧烈,眼里的活光很快收敛,又是一片垂死的神色,嗷嗷呜呜狗一样的叫声又从喉咙里涌出来。已经完全解除了心里负载的侄子们和林茂财大惊失色,骤然间意识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危机并没有根除,一下子又陷入更加沉重的二次打击中。
孙八指依然不慌不忙照前办理,重新在燃烧的烧酒的蓝色火焰里烧烤钢板和钢针。三个人不经吩咐已经分别挟制压死了老神头头手和腿脚。通红的钢针再次捅进喉咙,又是一股带着焦臭气味蓝烟。老神头又安静下来,继而眼里又放出活光来,这回他可没说话。
几个人的脸上和眼里的疑云凝滞不散。孙八指收拾起那只磨搓得紫红油亮的皮夹,重新系到裤带上,准备告辞。
家属们一齐拉住孙八指的胳膊,这样子你咋敢走?你走了再犯了可咋办呀?孙八指横着眉平板着脸说:“常言说,有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再不发生了算是他命大福大,万一再三再四地发生……我这两手也不顶啥了!”说罢就走出屋门走过院子走到街门外头来。
孙八指掖着皮夹走回他在白鹿镇上的中医堂以后,四个人把老神头团团围定。林茂财给病人喂了一匙糖水,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似的希望度过那个可怕的间隔期而不再发作。
老神头用十分柔弱十分哀婉的眼光扫视了围着他的三个人,又透过他们包围的空隙扫视了整个屋子,大约发觉孙八指不在了,迟疑一下就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就透出一股死而无疑的沉静。
他已预知到时间十分有限了,一下就把沉静的眼睛盯住儿子嘉轩,不容置疑地说:“我死了以后火化……骨灰不留,直接洒在山里。”
林茂财一愣,叹了口气说:“满江……先不说那事。先给你治病,病好了再说。”
老神头说:“我说的就是我死了的话,你当面答应我。”
林茂财为难起来:“真要……那样,也得好好办了丧事,这是礼仪。”
老神头说:“我这是报应,别人不清楚……你还不知道了?咱们林家几辈人旺财不旺。可到了我们这一辈子,我成了个单崩儿,好好我自己一家大小死了个干净……发丘盗墓,损阴德啊!”
林茂财的头上开始冒虚汗。
老神头说:“还有狗剩……”
旁边四小子一愣,随即火冒三丈地跳了起来大叫:“叔,你还惦着那个忘恩负义的小王八蛋?他早就带着宝贝跑了……”
老神头摇了摇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出了一口血沫子,然后微弱的喘息道:“那孩子不是那样的人,我清楚……”
四小子却是想起了原本到手的宝贝,不由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骂咧咧地说:“叔,你就别管了……我再遇到那个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
正僵持间,老神头又扭动起来,眼里的活光倏忽隐退,嘴里又发出嗷嗷嗷呜呜呜的狗一样的叫声,四个人顿时全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林茂财的一只手腕突然被老神头捉住,那指甲一阵紧似一阵直往肉里抠,垂死的眼睛放出一股凶光,嘴里的白沫不断涌出,在炕上翻滚扭动,那只手却不放松……
“爷,俺回来了?爷……”
正纠缠时,大门外匆匆一个人跑了进来,一进门就跪在了床头,正是刚刚赶到临别的笑天(狗剩)。
“爷!你这是咋的了……爷!你……”
像是深深叹了口气,老神头安慰的笑了起来,缓缓松了手,往后一仰,蹬了蹬腿就气绝了。
笑天一声哭嚎就昏死过去,被救醒时老神头已经穿上了老衣,香蜡已经在灵桌上焚烧。
林茂财说:“笑天,咱们先安顿丧事。你是他的老徒弟,少了你拿主意,旁的人也没法举动。”
笑天当即和几位长辈商定丧事,先定了必办不可的事情——几个家里人分头去给亲戚友好报丧,赶紧雇人联系纸扎和流水席面,派三四个帮忙的乡亲到集上买上供果和点心、把香、白布等一应物品。
下来就议到了乐人的事,这需得林茂财做主,请几个乐人?闹多大场面?继续多少时日?
商量了半支烟的功夫,事情定下来,让四小子到临近村里去找乐人班主,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个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就行了。整个丧事都按原定的程序进行。
七天后,老神头就在坟地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一个新鲜的湿漉漉的黄土堆成的墓圪塔没有按照他的意愿真去做那些撒骨扬灰的事——不管怎么说,林茂财也不愿意让兄弟魂飞魄散,人死为大,他倒不信这报应还没个头,能再应在他这里。笑天自然是更愿意按照传统办这个事,在他印象里,除了客死异乡,村里人基本上都是就近在坟岗子埋着的,这荒山野岭,没什么人来自讨没趣宣讲什么大道理。
这件悲凉的丧事总算过去了。
屋里走了老神头一个人,屋院里顿然空寂得令人窒息。如果笑天不咳嗽一声,这个有着两间房屋的院里整个晚上和白天都没有一丝声息。
四小子之后来过两次,咬牙切齿地要笑天把宝贝交出来,不过当时林茂财早早就得了信追过来,那四小子也只好干咋呼,倒没敢真动手。等到他第三次趁晚上来要债的时候,却是点灯熬油地和笑天聊了一晚上,具体说了什么不知道,但是临走时却是笑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连带着对笑天更是态度大好,甚至是毕恭毕敬了起来……